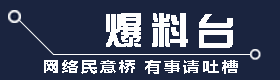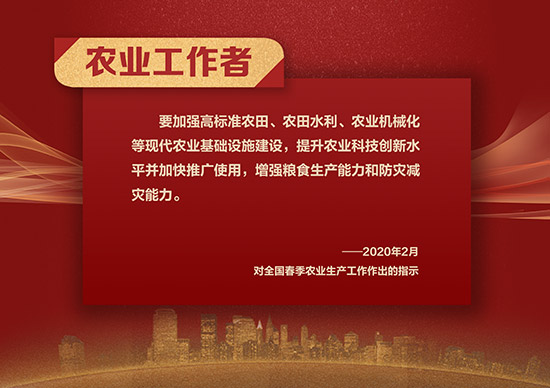●谭登会
下午下班一进门,母亲就对我说:“明天我们回趟家吧!”
我说:“前几个月不是回家了吗?”
父亲淡淡地说:“好久不回家了,都不记得家是什么样子了。”
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呢?我站在家的阳台上俯瞰一排排高楼,突然觉得它们像一摞摞整齐的作业本,而我所在只是作业本中的一个田字格,田字格里写着“家”字,横平竖直,撇轻捺重。工作生活都按部就班分布在固定的小格子里,是那样的条理分明。我想,翻开作业本我家的那一页,我应该用红墨水批注一个A+。
这就是我城里家的形状。
我知道父母所说的回“家”指的是老家。因为他们为了便于区分,一向把老家称作“家”,而把城里的新家称作“房子”。
我站在“房子”的阳台上,目光越过一摞摞厚厚的作业本,向“家”的方向延展。远山如墨,云雾缭绕,极像书法的飞白,“家”就在虚空留白的远方。家到底长什么样子呢?无论我怎样努力,都不能在脑海里形成关于形状的轮廓。比起“房子”的“田字格”来,“家”就像写在迷宫格里的字。
第二天,开车带上父母,回去看看“家”的形状。
院子是平行四边形的。原来住有九户人家,如今,院里没有一个人居住,有八家人的房子已破败不堪,剩下有两间木房,摇摇欲坠,柱子、屋梁、门板、楼板歪歪斜斜,像刚入学的孩子画出的粗细不均的线条,总是给人平行四边形的不稳定感。父亲说:“家都要倒塌了,看起来闹心。”
“家”是倒梯形的。在若干个不稳定的平行四边形中,我家却是一个稳定的倒梯形,屋脊、梁柱均端端正正,四周环绕各种树木、花草。倒梯形的格子里,木椅、木凳、八仙桌以及扫帚、蓑衣、锄头等摆放有序。
我耳际突然回响起当年父亲砍竹的叮当声、剥篾条的哗啦声、编蔑器的哔啵声,是那样的清脆。我似乎闻到了新篾的清香。我的童年是在这样的声响和味道里度过的。在这样的声响和味道里,细细拾掇家里每一本封面褶皱的书、每一片早已风干的叶子书签、每一张发黄的照片,眼中的“家”的形状时而清晰、时而模糊。
于是,“家”的形状又变成了万花筒。上山拾柴,下河摸鱼,和哥哥争夺连环画,得手后躲在柴草堆里小声咿咿呀呀,把玩母亲小时候上私塾用过的竹雕笔筒,阅读父亲赶场从亲戚家带回的报纸……童年的图案在我记忆的玻璃镜片上反射成像,稍稍把转一下,又是另外的图景。
当我的眼珠离开“家”的万花筒后,看见了瓦片上升起的炊烟。于是,“家”的形状变成袅袅的烟柱,在明净的天空里萦绕。母亲一到家,自然是钻进厨房,生火做饭。父亲嘛,仔细检查着每一根梁柱,每一面墙壁。这些年,换瓦、粉刷、加固,父亲一有机会,总是从城里的“房屋”往“家”跑。
吃完母亲做的农家饭,我们又得往城里赶。在村庄的后坡上,我停车看了看我的“家”。远处,白墙青瓦,掩映在郁郁葱葱之中,新硬化的泊油路像流动的线条,连接着房屋、田园和树林。
父亲指着那一排新房说:“那是刘家彭家的新家。他们的老家很快就要拆掉了。”他又指指我“家”说:“我们的家还保存完好,等明年春天我还要再培植些花草。”
随着清脆的汽笛声,我看见两辆银白的小车转过泊油路,在那新房子旁边停下了。
我知道,乡亲们回家了。他们也是要看看“家”到底长什么样儿了,并且和父亲一样,用勤劳和智慧描摹着“家”的形状。
感谢您关注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主流媒体重庆·石柱网,更多新闻关注其他主流媒体《石柱报》、《重庆石柱手机报》、“五彩石柱”微信公众号、“五彩石柱”APP、“石柱新闻”微博;统一投稿邮箱:sz_xwzx@sina.com。
总 编 辑:禹云洲
值班副总编辑:谭华英
执行主编:张俊杰